吕冰洋:央地行政关系的改革设想—寓分于集
时间:2020-02-24内容提要:顾炎武“寓封建于郡县”思想是:县域自治,强调它的活力;县以上传承郡县制,强调它的秩序。该思想有很强的合理性和操作性,据此可以提出央地行政关系的改革思路是:扩大中央政府职能,扩大县域自主权并升格,省级政府职能以行政监察权和官员升迁权为主。
前提:信息透明度增强、社会组织迅速成长
当前中国,央地关系有两个明显不同于古代社会的两个变化,由此对政府间组织形式产生两种重要影响。
第一,技术进步降低了央地间信息不对称程度,它会激发中央政府集权的冲动。
根据前文分析,中国央地关系的制度逻辑很多源自超大经济社会先天存在的很强的信息不对称,而人类社会进入工业革命后,技术进步呈现爆发趋势。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社会快速进入信息化时代,当前正在全球展开的信息技术革命,大幅度提高信息传递效率,这会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影响着社会变革的方向,也必然带来政府组织管理方式的变化。它典型体现在交通网与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上,它们大大缩小了信息传递时间,扩展了信息传递的内容,这使得央地间信息不对称程度大大降低,地方上发生的一些事情甚至可以瞬时为中央政府所掌握。
信息时代对央地关系构建所可能产生的影响有:随着上下级政府间、政府与社会间信息不对称程度下降,界定政府间权力与责任难度下降(命题三),政府组织效率会提高(命题四)。该影响容易激发政府集权的冲动,但是本文也同时指出,中央政府为提高组织效率的努力会抑制地方积极性,从而抑制地方活力(命题四)。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各项事业发展均离不了地方积极性的发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激发地方积极性,而在于激发地方政府什么样的积极性:是推动经济增长?提供公共服务?完善公共治理?吕冰洋、台航(2018)研究认为,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国应逐渐从激发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积极性,转变为提供公共服务积极性,未来更需要在地方层面实现以社会为中心的治理,社会参与和社会合作是必不可少的。
第二,社会组织迅速成长,需借力社会组织处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社会组织是集体行动的载体,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各种类型的社会组织迅速成长,据《中国统计年鉴》统计,自1990年至2016年,登记注册的中国社会组织由4446个增加到702405个,在登记注册的组织之外,还有大量的微信群、QQ群等依托互联网的新型组织存在,而它们的集体行动力量不见得低于传统组织。社会组织的发展对央地关系的处理产生两方面作用。一方面,社会组织起到简化信息、汇集意见的作用,它将分散的个人诉求转变为集体的诉求,降低了基层政府与原子式个人打交道所耗费的成本;另一方面,社会组织可以承担不少混合物品或服务的提供工作,从而协助地方政府对地方事务进行治理。在奥斯特洛姆(2012)的《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一书中,列举了大量的事例说明,集体组织完全可以有效地提供具有非排他性和竞争性的混合物品。我国自古以来也具有悠久的地方精英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传统,大量县级公共事务依托地方精英(如士绅)领头的各类组织(如宗族)推动(吴晗和费孝通等,2013)。
在我国古代基层治理策略分析中,有一种说法是“皇权不下县,县下皆自治”,县以下似乎出现“权力真空”,由士绅阶层为主导实现基层治理(温铁军,1999)。但是对该说法也有不少反对意见,秦晖(2005)认为,我国县以下存在着发达的基层组织,上级衙署所委派乡吏的职责十分广泛。胡恒(2015)的著作《皇权不下县?——清代县辖政区与基层社会治理》通过大量的史料分析,得出结论是中国古代县以下不存在完全自治现象,秦汉时期乡官、南宋以降的保甲和里甲组织、清代大量佐杂官等现象均说明国家政权在乡村的渗透。按照本文的逻辑,中国自古以来有很强的大国秩序依赖,为此,政府需要提高组织效率来动员和控制社会力量,县以下出现权力真空是不太可能的。只不过,由于大国的委托代理成本太高,统治者选择在保持国家一定秩序的前提下,政权从县以下收缩,而政权收缩留下的公共物品提供和公共秩序维护空间会由地方精英填补。这正是本文在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如何改造央地关系,促进地方精英成为“保护性经纪”而非“赢利性经纪”?
原则:县级行政单位强调活力 县级以上行政单位强调秩序
根据前文分析,在央地关系处理中,中央政府提高组织效率的努力在加强秩序的同时,却往往以降低下级政府和辖区社会活力为代价,那么如何兼顾活力与秩序这一对矛盾呢?对此,本文提出的央地关系处理原则是:县级行政单位强调活力,县级以上行政单位强调秩序。主要做法是赋予县级行政单位更多的自治权力,县级以上行政单位主要行使行政监察权和官员选拔权,这取法于顾炎武“寓封建于郡县”的精神。其好处有三点。
第一,有利于激发基层社会活力。中国国土面积广大,不可能像小型国家那样可以将很高比例的人口集中在大都市,大多数的人口、经济和社会活动要在县域层面展开,自古有言道:“郡县治,天下无不治”。目前,我国县域人口大约10亿,占全国人口总数的77%左右;县域GDP约占全国经济总量的60%;县域国土面积约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92%。县级单位直接面对基层社会,先天地具有了解基层社会的信息优势。根据命题二,如果给予县级行政单位更多的自治权力,减少上级政府对县级具体行政事务的控制,那么会使得县级政府更能准确地反映辖区居民偏好,有助于激发基层社会的活力。反之,如果过度强调对县级单位的控制,根据命题三,在上级政府相对基层政府具有信息劣势的情况下,实际上事权是永远无法清晰地被界定,其结果是对基层政府和社会的控制要么效果不佳,要么以降低社会活力为代价。
第二,有利于维持纵向政府间权力秩序格局。自古以来,对中央权威造成挑战的力量主要来自省级及以上单位(对应的行政首长如侯王、节度使、总督等),县域单位规模太小,对纵向政府权力秩序格局造成的影响很小(命题五)。赋予县级单位更多自治权力后,就可以减少县级以上行政单位的事权,而将事权更多集中在监察权力上,其监察权力范围也可大大缩小。由于监察权力的集中和范围缩小,就可以大大降低信息复杂性和不对称性程度对组织效率下降的影响(命题四),同时也可以减少县级以上行政单位的行政规模,降低中央政府的信息处理成本(命题五),而这一切均有利于维持纵向政府间权力秩序格局。
第三,降低政府规模,降低行政运转成本。县级单位拥有更多的自治权,这意味着自上而下的层层监察机构减少,“管官的官”也会随着减少。同时,县以上单位的事权的减少,也意味着财政供养人口的减少。这样,顾炎武所痛言的“大官多、小官少”的现象也会随之减少,总体政府规模就会降低,行政动转成本也会下降。
为什么不应在省一级而应在县一级赋予更多自我治理权力?现代政治实际上是在委托结构(commitment stucture)和问责过程(accountability processes)之间取得平衡(Bardhan, 2016)。以选举权为代表的自我治理权力下放,虽然有助于约束政府权力,但不一定会让政府更加有效地回应地方层面的信息、主动性和创新性。研究指出,在省级层面的选举,会使得省级政府更多精力集中在协调地区或不同群体的差异性上,而不会更多回应基层社会的需求(Seabright, 1996)。因此,应扩大县级而不是省级的自我治理权力。
方案:哑铃分权,寓分于集
基于以上原则,可以确定央地关系的改革方案是:哑铃分权,寓分于集。“哑铃分权”的合理性在于:中国作为一个超大型国家,一方面各项事业发展必须有强大的中央政府才能得以推动,另一方面绝大多数经济和社会活动在县域层面展开,发展县域经济、激活县域社会活力是国家固本强基的正道,为此需要在政治经济制度安排上,赋予县级政府更多权力。“寓分于集”的合理性在于:一方面建立强大中央政府必须实行中央集权,而中国在悠久的郡县制传统中有很多治理经验可供借鉴;另一方面,要激发基层社会的活力,又必须在县级实行广泛的分权。这可以说是当年顾炎武“寓封建于郡县”的思想精义所在。
具体措施如下:
1. 强县:扩大县域自主权,县级政府升格
一是落实《宪法》和《地方组织法》原则,支持和保证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对行政首长的监督权和任免权。
地方主政领导的行为偏好是否能反映当地居民的需求,对地方公共治理效果产生重要影响。而我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地方组织法》中,已经有了比较好的制度设计。宪法赋予了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和罢免同级政府首长的权力,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也进一步强调了“支持和保证人大依法行使立法权、监督权、决定权、任免权”,以及“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在《地方组织法》中,规定地方国家机关正职领导人的选举标准为:“候选人数一般应多一人,进行差额选举。”在主政官员任用中引入竞争因素,会促使地方主政领导的偏好与辖区居民偏好保持一致。
落实宪法和地方组织法原则,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让县级行政首长的任免和权力行使更大程度上受同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制约,最大程度解决地方官员面临的“事上”与“安下”一对矛盾。在现实中,“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习近平,2015),县委书记对县里各项公共事务具有很大主导权,对此,需要加强党内民主、党内选举、党内监察等制度创新,促使县委书记决策符合当地社会的合理预期。
另外,行政首长的任期与任期预期对行政首长的执政行为影响很大,据研究,现实中大多数县级行政首长任期不满一届,平均为3.25年(罗中枢、王卓,2011),因此要落实好宪法所确定的行政首长任期制,让县级行政首长从地方公共事业发展中获得更多的成就感和奖励。
该做法类似如顾炎武所言,“设世官之奖”。
二是有关县域公共事务尽量将事权下放给县里,县域获得更大范围自主权。
对外部性小、地方具有信息优势的公共事务,如义务教育、卫生、市场管理等,可大量地下放到县里,这有利于发挥县级政府的积极性。该做法类似如顾炎武所言,“予之以生财治人之权”。
三是县主要领导升格为正厅级,县里职能部门升格为正处级,取消股级。
目前县长和县委书记属于正处级,部分重要县为副厅级,这在目前行政序列里属于比较低的职级,不利于体现县域治理的重要性。县长和县委书记是正处长级,县里所管辖的人口常达几十万之多,这是中央部委各部门处长面临的事务所不能比的。公务员在市以上机关可以一步提拔到科级,而县里只可以提拔到股级,这种不平等或不平衡情况应取消,在行政序列里提升县长官及相应职能部门的职级。
该做法类似如顾炎武所言,“改知县为五品官”。
2. 强中央:扩大中央政府职能
中央政府集中一定的权力,具有如下好处:有利于政令畅通,避免地方挑战中央权威;有助于维护市场统一,避免地方政府间竞争造成市场分割;有助于集中和分配资源来协调地区发展,避免地区差距过大。在中国这样具有广大国土、地区间差异巨大的国家,增强中央政府的职能、增强中央政府的权威尤其重要。在过去,大量政治学和经济学著作对中央集权的正向作用要么不提及,要么持有反对态度。但是,最近若干年,一些重要研究认为,中央政府集权有助于提升国家能力,它实际上是与产权保护制度一样,都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福山,2015;阿西莫格鲁、罗宾逊,2015)。中央政府的集权程度与中央政府的职能行使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相比其他国家,目前我国中央政府的职能偏少和偏小,以中央政府公务员占全国公务员比重为例,我国只有6%,很多国家在30%以上,经合组织成员国平均为41.41%(楼继伟,2013);再如中央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我国每年基本在15%左右,而2015年OCED组织平均为47.02%。
为建立强大中央政府,可主要采取两点措施。
第一,中央政府保持对省级政府人事任免权和行政监察权。中央政府人事任免和行政监察可有效地控制地方政府行为,这实际是我国自实行郡县制以来一直采取的作法,但是历史上也多次出现地方挑战中央权威的现象,原因在于当中央政府对地方事务鞭长莫及时,需要下放一些权力到省级政府,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权力一旦下放,中央政府再想收回就很困难。因此,需要借鉴中国传统郡县制治理思路,从中央到省,强调集权和政令统一。
第二,在财政上要承担更多的事权,并通过集中财力和大规模转移支付来协调地方发展。中央政府承担更多的事权,意味着它对资源的掌控和调配力度增强。中央政府集中财力并实行大规模转移支付,意味着地方政府不少资金来源于中央政府。人事和财力是权力的两大重要来源,当中央政府控制这两项时,中央政府组织效率提高、和相应国家能力提升就有了保障。
3. 取消地市级政府
我国地市级政府是横亘在省和县之间的政府,在行政序列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就是这样重要的一级政府,长期以来却处于法理不明确的位置。我国宪法明确规定“我国的地方政府分为省县乡三级。”因此,从法理上看,地市级政府不是地方政府。它最初是作为省级政府的派出机构存在的,是代表省级政府指导县级政府工作。在交通不发达、信息交流成本较高的年代,地市级政府可以起到解决省级和县级政府信息不对称、提高组织效率的作用,但是也随之带来政府规模膨胀、政府冗员增加、财政负担加重、市县争利的局面。
目前地市级的职能主要有两点:一是承担地市级公共事务的管理,二是对县级政府进行监察。如果县域实行自治,那么大量的事权就集中在县级政府,对县级的监察权力要么可取消,要么可归为省级政府。在这样的背景下,可彻底取消地市级政府。
取消地市级政府也有很大的现实可行性。自2005年起,我国开始推行“省直管县”改革,目前据可查资料,全国共有27个省(市、区)对1080个县实行财政直接管理,顺此可逐渐将人事权、审批权、监督权上收到省级政府。从政治操作性出发,取消地市级政府并不需要调整地市级干部队伍,而是让县级升格与地市级平级,两者无隶属关系,这自然会达到取消地市级政府的效果。
该做法类似如顾炎武所言,“罢监司之任”、“其督抚司道悉罢。”
4. 省级政府职能以行政监察权和官员升迁权为主
我国以省为地方行政单位的制度来自元代。元代中央行政机关叫“中书省”,在地方上设“行中书省”,意思是它们是中书省派出的机关,简称“行省”,最后简称为“省”,明清也就承袭这一制度并延续至今。
从中国历史经验看,省级政府的管辖范围和管辖权力均有过大之嫌。我国各省平均管辖面积为3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如英国和德国这样中型国家的面积。由于省管辖范围大,可调动的资源多,为避免省级政府成为潜在对抗中央政府的力量,中国历史各王朝在初始时,一般都大力消弱省级政府的权力,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地方事务越来越复杂,省级政府权力会逐渐扩张。一旦中央政府权威下降,省级单位(包括总督两省甚至更多的单位)就可能违抗中央政府的命令,导致政令不通。为此,省级政府的改革方向为两点:
第一,减少省级政府事权。事权体现着政府职能,有两点可能使得省级政府事权减少,一是按照强县的思路,可把发展地方社会经济的事权大量下放到县级政府,二是在信息化时代,中央政府的管理半径实际上得到了延伸,跨区域的公共物品提供可以由中央政府协调地方完成。
第二,省级政府以行使监察权和升迁权为主。当赋予县级政府较大的自治权后,县级政府行政将以辖区利益为重,就可能存在局部利益与全部利益相抵触的情况,因此需要在法律上明确县级政府行使权力的边界,并由省级政府进行监察。其本义也是要有监察专员监督县级政府的行为。如果省级政府认为县长官工作实绩较好,就可以将其提拔到省政府。但是省级政府不能有罢免县级官员权力,因为县级长官由同级人大选举产生,只要辖区居民认可官员行政水平,省级政府就没有理由罢免县级官员。
该做法类似如顾炎武所言,“诏遣御史巡方”。
县以上政府,应不是基层社会冲突的责任承担者,而是冲突的化解者。对省级政府而言,负有监察县级政府行为的权力,同时也受中央政府和同级人大的严格监督;对中央政府而言,要通过权力制衡、党内监察、人大监督等约束权力。
以“哑铃分权,寓分于集”为特点的央地关系改革方案,使得央地权力关系变为:权力两头重、中间轻;县级自治,县上集权。这样设置的好处是:减少政府级次,使得政府间政令更通畅;强化中央权威,消除未来省级政府经济扩张和权限过大带来隐患;县级政府直接面向当地市场和社会,有利于发挥县级政府积极性,促进县域治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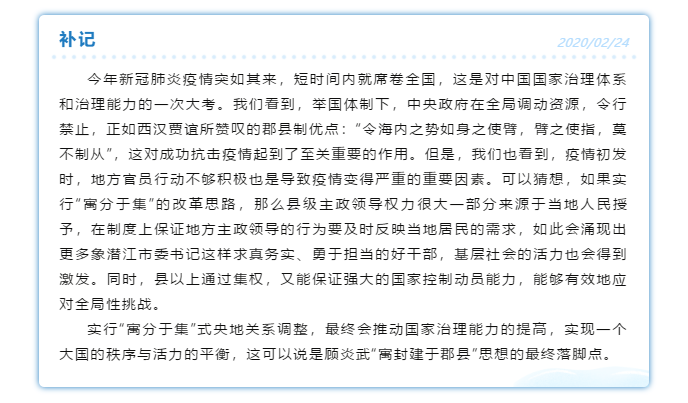
文章来源:《财贸经济》2019年10期,原文标题《“顾炎武方案”与央地关系构建:寓活力于秩序》,本文为原文内容节选

